大国将令2024年11月14日发布:当代文学史料发掘与研究|程光炜:材料改变叙述——关于当代文学史料应用的思考
作者:董颖 | 责任编辑:Admin
本次大会汇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科技领袖,共同探讨未来科技趋势...
【新澳门开奖历史记录走势图表】 |
【2024新澳门免费资料】 |
| 【新澳精准资料大全免费更新】 |
| 【澳门天天彩资料正版免费特色快8】 |
| 【新奥天天免费资料的注意事项】 |
| 【澳门六开彩天天正版澳门在线】 |
| 【新澳免费资料网站大全】 |
| 【新澳最新最快资料22码】 |
| 【新澳2024年精准正版资料】 |
| 【澳门正版挂牌免费挂牌大全】 |

程光炜
最近一些年,我在关于文学史材料的会议上,听过有的学者谈到“材料改变叙述”的观点。具体点说,就是这些材料对历史结论产生了瓦解、颠覆的作用,虽然,它目前只是在某一领域和局部发生。最近我阅读材料,看到苏联作家爱伦堡重印版的《人·岁月·生活》(上、下卷,海南出版社2008年版)。据蓝英年《译本序》说,爱伦堡1960年开始写这部回忆录,在《新世界》杂志陆续发表,直到1964年才载完,后结集出版。该书出版后,在“读者中引起了热烈反响”,产生了轰动效应,苏联也由此掀起了“爱伦堡热”。1990年莫斯科作家出版社还出版过装帧精美的三卷集,由于每页下角有配合内容的图片,可以“当作史书读”,因为苏联作家中“谁也没有他那样的经历”。[1]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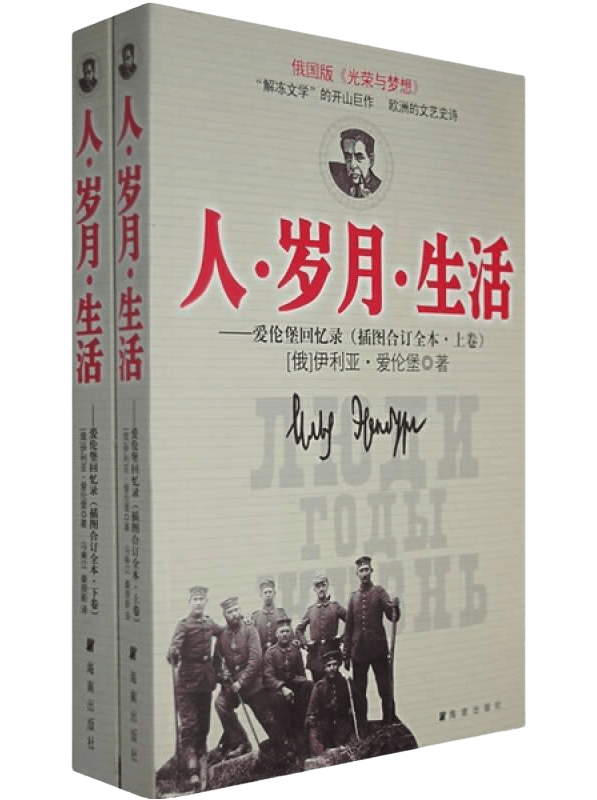
《人·岁月·生活》(上、下卷)
[俄]伊利亚·爱伦堡
冯江南、秦顺新译
海南出版社
2008
发生这样的情况,可以说是苏联历史的变故所致,当然在其它地方,很难出现相类似的情况。这说明,当代文学材料也处在变迁的过程之中,这样就造成了“材料改变叙述”的可能。对于中国文学来说,这个问题贯穿了20世纪上半叶的现代文学。现代文学之所以在不断发现新材料,找到新版本,并由此形成对某一结论的质疑性的看法,正说明人们认为“现代时间”还没有停滞、结束、静止。这一历史惯性,明显也传导到了中国当代文学当中。
为此,我想起某次为本科生讲授“中国当代文学史”时列举的两个例子:
一个例子是丁玲、陈企霞主持的《文艺报》,从1951年6月第4卷第5期开始,《文艺报》用将近半年时间对萧也牧小说《我们夫妇之间》开展批评。因教学需要,也因为要写研究萧也牧的文章,我花了点时间查找相关材料。与此同时,我也读了一批研究丁玲、陈企霞的论著、传记和回忆性的材料。通过读材料,我隐隐约约发现那里面隐藏着一个“真相”,这个“真相”是,在1951年文艺界整风的时候,作为“学习委员会主任”的丁玲,在协助上面工作的同时,还掌握着《文艺报》这个阵地。因为身负重任,丁玲需要找“典型”,而当时,萧也牧随着《海河边上》《我们夫妇之间》等一二十篇小说的发表,正受到广大城市青年读者的欢迎,风头很健,其影响力甚至有超过赵树理、孙犁和丁玲等人的趋势。这个情况受到丁玲的注意。不可否认,萧也牧小说《我们夫妇之间》在描写老干部的夫妻关系上,确实存在着一些漏洞。比如,李克夸张性的语言、某些人物对话里含有讥讽语气——虽然不能算“本质”问题,上升不到“倾向”的高度,但令人不解的是,他却被《文艺报》选为“典型”。在丁玲、冯雪峰和陈企霞的合作下,这篇小说受到了严厉批判,萧也牧从此开始走下坡路(行政级别由11级,降为13级。“反右”后降到17级,连家庭生活都受到影响),他1970年在干校农场过早病逝,不能说与这次批判毫无关系。但是在当代文学史的叙述中,丁、冯、陈是以“受害者”的面目出现的,没人会想到,他们也曾做过隐秘的“加害者”。一定意义上,这个材料对三位人物在文学史中已经固化了的历史形象,确实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。人们可以说,丁玲的行为是由于工作需要,但她也不一定非得要如此做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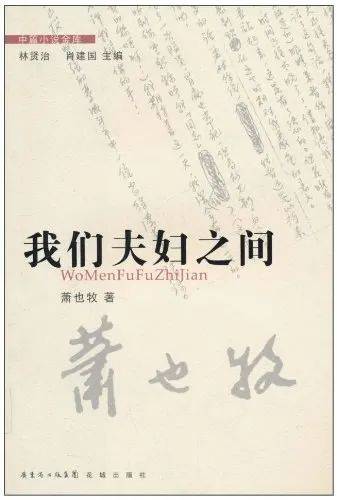
《我们夫妇之间》
萧也牧
花城出版社
2010
记得两年前,我在一所著名大学讲跟这个材料有关的一篇文章时,有的老师提出了不同意见,认为我“矮化”了丁玲,没有顾及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“合理性”因素,也即历史的逻辑本身。我能理解这种质疑。在读《人·岁月·生活》这本书的时候,我当时一方面沉浸在作者对复杂、多元、多变历史生活的讲述中,与此同时,也极力想摆脱出来,用现在的话说,是“超越”出来,但实际上很难做到。在最近发表的文章《选题的直觉》[2]里,我也谈过自己这种困难的处境。一个历史研究者,由于个人经验的不同,站的角度不一样,他与历史“同感”的程度也会明显不同。不过,虽然中外史学理论在研究历史学者与历史的关系时,曾发表过许多五花八门的观点,然而,在潜意识里,在他们所感知和分析的“历史”深处,依然有一个“历史标准”。就我目前的感受说,对于当代文学,这个问题似乎还显得比较遥远、渺茫,但也不至于悲观。
第二个材料跟作家邓友梅有一点关系。1950年5月25日出版的《文艺报》第2卷第5期,登出三野文工一团团员邓友梅批评《说说唱唱》上小说《金锁》的文章《评<金锁>》(作者1957年因小说《在悬崖上》被错划为“右派”,新时期被称作“归来作家”)。这个材料相对好玩一些。在人们印象里,邓友梅只跟“右派”“归来作家”等等符号挂钩,因此,在他身上,有一种特殊的、浪漫的、悲剧性的色彩。没想到,他竟和竹可羽一样,是1950年代初最早批评赵树理的人之一。在这篇指责赵树理担任《说说唱唱》主编时编发的作品的文章里,他“夹枪带棒”地讽刺了这个已被确定为“方向”的名作家:“我记得赵树理同志写的《李有才板话》中的李有才也是一个劳动诗人,他唱出来的歌成了斗争的武器,这位劳动人民的智慧是通过斗争表现出来的”……文章接着来的重点是这句话:“但是金锁所唱的是什么东西呢?”我猜他没说出的话是,你一个“进步作家”,怎么编选了一篇“落后的作品”呢?不单这件事,邓友梅那时在报纸上表现得很活跃,比如,写过《关于武训的一些材料》这类刺眼的短文……当然,我得承认,看到这些材料,心中难免会产生一点沮丧的感觉。因为从上大学起,直到几十年来在大学讲授当代文学史的课,一直对“归来作家”们的患难经历抱持着极大的同情态度,甚至有些崇拜和敬佩,在讲课时,自己有时候还比较激动,自然——这也是为了“感染”听课的学生——之所以长期如此,可能是因为我,还有不少同行,都对这种历史大叙述深信不疑的缘故罢。从来没想过,如果不听信传闻、传言,而去摸一摸多年前的材料,说不定还会有更“奇怪”的事情发生,至少,不再简单相信大叙述的说辞了。虽然这个材料对“归来作家”整体历史观的“颠覆”,不能说是很大,但至少也不能算是小罢——我这样说,不是要否定过去所拥有的历史记忆。不过,我仍然相信,“材料”在有的时候、有的条件下,也确实可以改变某些看起来已经很是坚固的“叙述”。
前一个例子是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作家“重评”的“再重评”问题。它的含义是,丁玲、冯雪峰在错误文艺思潮的影响下,蒙受了不应该的劫难。然而,这种“重评”同时在遮盖他们曾经在错误思潮中利用自己的地位、影响,对另一些无辜者造成的劫难。现在有一个现象,就是对丁玲、冯雪峰等“蒙难者”形象的维护,这变成了一个不能动摇的结论。由于有各种作家研究会的制度保障,对新材料的发掘和研究,似乎也正在成为新的“异端”。这一现象对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,显然是不利的。后一个例子,与前一个例子有共同点,但稍有不同——即“受害者”不能再作为“加害者”来处理。在新时期文学和作家研究中,这种与他们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史相“割裂”的倾向、相矛盾的现象正在叠加。这种叠加所产生的结果是,只能强调他们与过去历史的“对立”。当然,我能够想到的背景是,在旧的历史终结之后,新的历史叙述总会把“重评”当作自身合法性的立足点。目前的当代文学教学、当代文学研究,还无法摆脱这一习惯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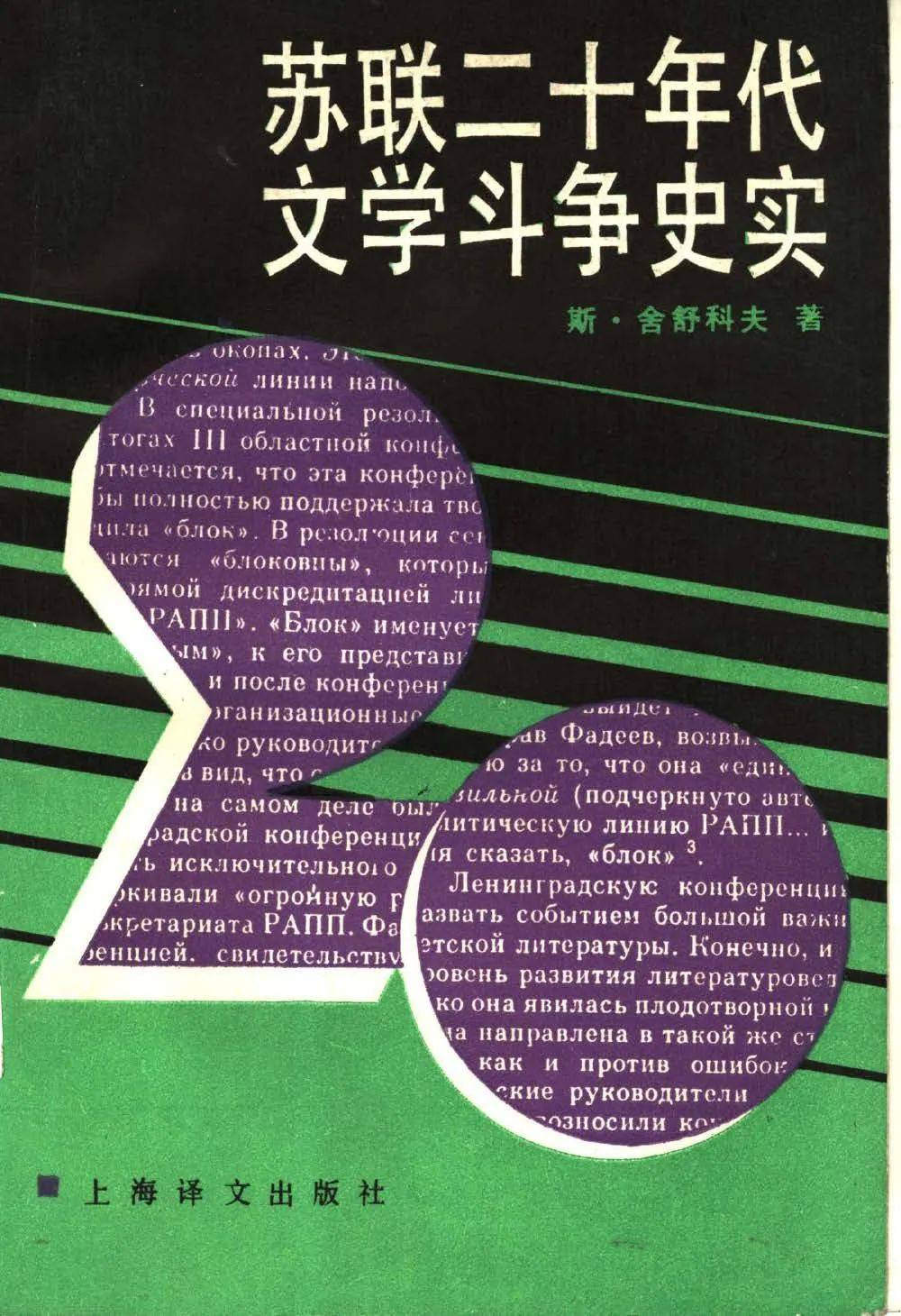
《苏联二十年代文学斗争史实》
[苏]斯·舍舒科夫
冯玉律译
上海译文出版社
1994
但是我们知道,要克服这些障碍,首先就需要历史的距离。苏联学者斯·舍舒科夫的《苏联二十年代的文学斗争史实》1984年出版,到1994年,冯玉律先生的新译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,与中国读者见面。这本书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文学的史实,做了相当充分的介绍。比如,苏联当代文学“无产阶级文化派”“拉普”“莫普”“锻冶场”“岗位派”等大大小小的文艺派别先后登场,霸占文艺界舞台,以“过于热心捍卫无产阶级纯洁性”,或说“纯而又纯”的激进姿态,排斥其他的文学主张、流派、作家,甚至排斥“托尔斯泰传统”,以致发展到与处于主流的《共青团真理报》的公然对抗、叫板。最后,到了1932年,联共(布)中央不得不出面,发表《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》的决议,成立俄罗斯联邦苏维埃作家协会组织委员会,并强调“苏联全体文艺届知识分子”的团结,才将它们逐出了文艺界。这段史实发生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,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斯·舍舒科夫才写出这部具有“反思”性的著作。正如作者在该书《前言》里声明的那样:“现在,我们国家已经成立了六十多年,理智从这样的高度要求我们摒弃一切不公正的、外加的、偶然的因素,尽可能平心静气地、客观地、以主人翁的态度来把我们这部复杂而又极为丰富的文学史弄清楚。”“只有通过这样的研究才能达到主要的目的——弄清真相,对苏维埃文学史作出合乎实际的阐述。”[3]正如他所言,由于历史已经拉开了距离,所以“理智从这样的高度要求我们”……

《毁灭》
[苏]法捷耶夫
隋洛文(鲁迅)译
大江书铺
1931
这本书有意思的地方很多,其中最吸引我的,是对苏联当代著名作家法捷耶夫没有被“割裂历史”的全面研究。中国读者都熟悉法捷耶夫(1901-1956)这个人,他曾任苏联作家协会总书记,在苏联文化界可是一个大人物,实际也是当代文学的“常青树”。他1922年以中篇小说《泛滥》崭露头角。1927年,他创作的长篇小说《毁灭》引起轰动(鲁迅曾翻译此作[4]),代表作还有《逆流》(1924)、《最后一个乌兑格人》(1929)、《青年近卫军》(1945),另有《在自由中国》(1949)、《论鲁迅》(1949)和《三十年间》)(类似“文学回忆录”。1956)等。他1918年在远东加入工农红军游击队,1921年出席俄共(布)第十次代表大会,1926年担任“拉普”(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)理事会执行局成员,对其他“非无产阶级文化派”的文学社团、组织、流派和主张,进行过言论攻击。直到1931年,作为“拉普”主要领导人的他,还从“宗派”立场出发,站到了与《共青团真理报》对抗的最前列。不过,在联共(布)《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》决议公布后,他很快承认了“错误”,不久成功“转型”为新成立的作家协会的领导人之一,1946年成为协会总书记。1954年,赫鲁晓夫以“疗养”为名,解除了他的作协总书记职务,但保留理事会主席一职。因遭遇严重挫折,以及对“解冻思潮”思想上有抵触,1956年3月,他在“家中开枪自杀”。苏联政府对外宣称他是“死于酗酒”。1990年,这份档案被公开解密。这本书的作者利用大量和丰富的档案材料,对这位对苏联当代文学作出了巨大贡献,在文艺思想上又存在争议的著名作家,不讳言,不掩饰,有好说好,有坏说坏,不仅没有降低、削弱他的地位和形象,反而使他的历史活动更为真实。该书提供的有益经验,值得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人汲取。
当代文学的情况与前苏联不同,它还在延续。像爱伦堡这种等级的人物,没有留下有分量的材料(夏衍的《懒寻旧梦录》被个别老作家家属认为“不真实”),即使流于市面的东西,情形也大同小异。重要档案难以查阅、搜集、求证,虽然在可以公开的文艺报刊上,残留着不在少数的信息,不过,阅读材料的人,却不可能顺藤摸瓜,进行深入且具有建设性的研究。张均前不久发表的《档案所见若干当代文艺接受史料》,利用多家地方档案馆的史料,分析了不同受众在红色文艺接受过程中的各种反应。他说:“这些存留在档案深处的声音,映射出……内部无法修补的裂缝。”[5]出现这种情况,一个直接原因是“历史”还没有“拉长”(有些欧洲学者持这种观点,只有历史学家的“心情平静”下来,才能做法国大革命的研究。而实际情况是,目前出版问世的诸多相关著作,作者却都是带着不平静的心情完成的),同时这说明当代文学的材料建设空间,还有拓展的必要。尽管如此,对夏衍这本书,我仍然难以像读《人·岁月·生活》那样有“丰富的反应”,不知是什么原因。
前一段时间,为参加一个专题研讨会,我写了一篇题为《周扬的“两面性——<周扬文集>一至四卷发表和未发表的文章》的发言,其中提到,“《周扬文集》[6](人民文学出版社)1949至1965年的文章,收在一至四卷,总计104篇,公开发表23篇,未公开发表81篇。具体的情况是:一卷公开发表1篇(1949),因该卷多是他1929年至1948年的文章;二卷公开发表16篇(1950-1957);三卷公开发表4篇(1958-1961<上>);四卷公开发表1篇(1961<下>-1965)。二卷未公开的文章16篇;三卷未公开的文章29篇;四卷未公开的文章36篇。“文集”编选者对它们的处理是,公开发表的文章在下方注释“本文载于”某年某报刊,未公开发表的文章则注明是在某年某次会议上的“讲话”,“未公开发表过”;另一些文章未加注释,我们由此判断也未发表。由简单统计的情况看,1950-1957年间发表和未发表的文章均为16篇,两项持平。1958-1961(上)只发表4篇,未发表29篇,两者之间严重失衡。1961(下)-1965年公开发表1篇,多达36篇未发表。这种情况是由于编稿原因,还是其他缘故,文集的“出版说明”未做解释。为此我提出一个问题:“公开发表”和“未公开发表”之间的界限、标准究竟是什么,包含着什么具体信息?由于文章注释没有解释,当然也不会有真正的答案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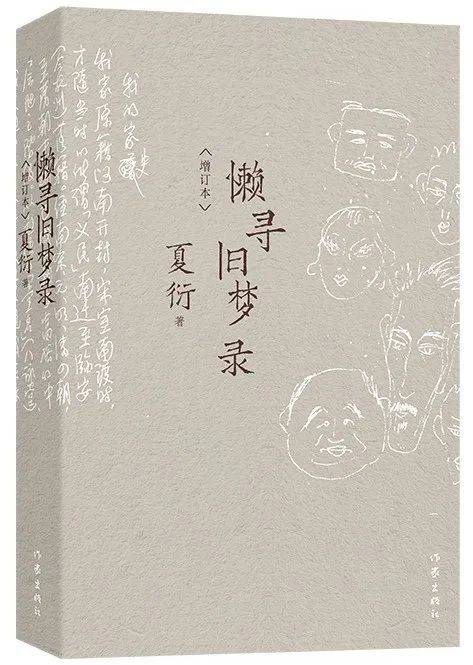
《懒寻旧梦录》(增订本)
夏衍
作家出版社
2022
当代文学是一种深度介入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及以后中国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活动当中的文学样态,里面有中外关系、冷战、社会改革和各类事件,有不少当事人的思想感情,在这一过程中,也夹杂着大量的还没有触及的“私人生活”(在这“一切都聚焦于普通人生活中的几个瞬间,历史几乎不会涉及这些内容”——阿莱特·法尔热语)。[7]比之有人对《懒寻旧梦录》的“遗憾”,比之我在阅读《周扬文集》编辑材料时没有看到的“下文”,以“材料改变叙述”作为话题还显得有些轻巧,不过,它作为一个探索性路径、一种眼光,依然能够给人以启发。我最近读小说《解冻》(1982年重版)、《苏联文学史》上下卷(1957)、《五十、六十年代的苏联文学》(1974)、《必要的解释》(1982)、《关于<解冻>及其思潮》(“内部发行”,1982)、《西方论苏联当代文学》(1982)、《法捷耶夫评传》(1959)、《苏联作家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》(1960)等一批“材料”,老实说,我常常为它们能否“改变叙述”这个问题所困扰。不过阿莱特·法尔热在《档案之魅》中却说,“研究档案的学者常常会用潜水、淹没甚至溺水这样的词汇来描述这段探索旅程”,“那种朴素但深沉的感觉油然而生,就像揭开了一层面纱,穿过了认知的迷雾,经历了一段漫长而不确定的旅程后,终于了解到生命和事物的真谛”。[8]然而有时候,人会想到,“叙述”也可以“改变材料”。比如1957年,当西方学者对“苏联文化”普遍产生怀疑的情况下,《必要的解释》里有这么几句话,它们是:“在我们这个复杂而又不易理解的时代,必须学会看得广泛和长远。苏联文化不是一现的昙花,它是历史上的一种重大现象,不是发一阵牢骚和怨气就能把它抹煞的”,“我们的一切成就,正如同我们的一切失败一样,都应该这样来解释……我们是在写作,而不是抄写……”[9]
2024.7.28
次日再改
本文根据程光炜在中国人民大学文艺思潮研究所2023年6月召开的“文献史料与当代文学史的教学问题”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。
注释
[1] [俄]伊利亚·爱伦堡:《人·岁月·生活》(上、下卷),冯江南、秦顺新译,海南出版社2008年版,第2页。
[2] 参见程光炜:《选题的直觉——当代文学四题》,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》2024年第4期。
[3] 苏联学者能够写出这种著作,与该国后来的历史变迁所提供的写作环境有一定的关系。从该书的材料看,作者也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,同时对文学史发展的脉络也比较熟悉。
[4] “鲁迅《毁灭》译稿”,是许广平1950年捐赠的。1929年下半年,鲁迅根据日本藏原惟人的日译本重译《毁灭》,连载于1930年1月出刊的《萌芽》月刊,至第四部第四章被禁。后来鲁迅参照德文译本,1930年底译完全书。1931年9月30日《毁灭》由大江书铺出版,此为我国最早的中译本。
[5] 张均:《档案所见若干当代文艺接受史料》,《文艺争鸣》2024年第5期。
[6] 《周扬文集》第一卷出版于1984年,全部五卷直到1994年才出齐。周扬1989年7月已去世。
[7] 前几年,我的一位老学生曾推荐过一篇研究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人“日常报刊书籍消费”的文章,该文章属于社会学领域,但对研究当代文学的阅读、接受依然有不小的帮助。另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英国学者奥兰多·费吉斯的《耳语者: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》一书,也值得一读。
[8] [法]阿莱特·法尔热:《档案之魅》,申华明译,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,第2、5页。
[9] [苏联]伊里亚·爱伦堡:《必要的解释(1948-1959文艺论文选)》,北京大学俄语系俄罗斯苏联文学研究室编译,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,第91、93页。
《史料的前途》
程光炜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2024
扬子江文学评论
2024年第5期目录
名家三棱镜·付秀莹
付秀莹|一些闲话
葛水平|小说家是目光,也是景色——付秀莹和她的小说记忆
马 兵|“常”与“变”之下的心事、节气、言语与风景——论付秀莹的芳村书写
当代文学史料发掘与研究
程光炜|材料改变叙述?——关于当代文学史料应用的思考
易 彬|年谱撰写的文献之道——从《彭燕郊年谱》说起
李广益|又一个十年:史料学视野中的中国科幻研究(2014-2024)
思潮与现象·素人写作
项 静|素人写作:时代文体与经验的公共化
张慧瑜|家政女工的四个“家”:劳动、性别与文学书写
霍 艳|“素人写作”的跨媒介传播与内核变异
新作快评
赵月斌|永恒少年的假胡须——读张炜《去老万玉家》
文学史新视野
尹 林|“科学文艺”与改革开放后类型文学预案
黄锐杰|错位的“五四”——由1958年文集版《家》的一处修订谈起
顾绅楠|“文化大散文”何以入史——从一个概念重返1990年代
作家作品论
王彬彬|汪曾祺早期小说片论
张 涛|“很多时候,恋爱是用来对抗伤痛的”——读叶弥《不老》
苏 也|空间生产与不可靠叙述——论《河边的错误》的跨媒介改编
周 燊|发声于修辞之外——王蒙散文的新古典主义抒情形态探微
扬子江文学评论
邮箱|yzjwxpl2020@163.com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责任编辑:
| 【管家婆一码一肖资料大全一语中特】 | 【新澳门正版免费大全】 | 【2024新奥天天免费资料】 | 【新澳正版资料免费提供】 | 【新澳2024今晚开奖资料】 | 【新澳精准资料免费提供】 | 【新澳门今晚开奖结果+开奖直播】 | 【2024新澳正版免费资料】 |
推荐文章

三年级功课不好,要不要停掉兴趣班?
1929年下半年,鲁迅根据日本藏原惟人的日译本重译《毁灭》,连载于1930年1月出刊的《萌芽》月刊,至第四部第四章被禁。...

小说:少年被狙击枪锁定,竟然口出狂言,看你的枪快还是我快
后来鲁迅参照德文译本,1930年底译完全书。...

伊万卡夫妇不会重返白宫
马 兵|“常”与“变”之下的心事、节气、言语与风景——论付秀莹的芳村书写 ...

彭文生:需要从根本上反思财政政策理念
与此同时,我也读了一批研究丁玲、陈企霞的论著、传记和回忆性的材料。...
最新评论
丹尼尔·逊亚塔 2024-11-13 24:23
现代文学之所以在不断发现新材料,找到新版本,并由此形成对某一结论的质疑性的看法,正说明人们认为“现代时间”还没有停滞、结束、静止。
IP:55.82.8.*
乌戈·席尔瓦 2024-11-13 16:23
1994
IP:99.59.2.*
郑米楠 2024-11-13 14:17
具体点说,就是这些材料对历史结论产生了瓦解、颠覆的作用,虽然,它目前只是在某一领域和局部发生。
IP:61.96.3.*